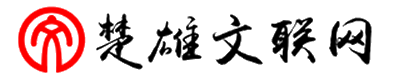作者:钱静
1
院门右边的路上,站着一个人,眼睛看着我们这边,细看,是郑小泉。村里的人背地里说,他神经有问题。他呆呆傻傻的,几乎不说话,你跟他说,他只会笑。听说,他五年前去了十多公里外的天坑,才变成这个样子。有人说,他被天坑里的怪物吓傻了,有的说,他中了坑里的毒气。人们问他,进天坑看见什么、闻到什么,他笑而不答。
矮处手臂粗的枝干锯掉了。以前,我只能爬三米高,今天到五米就不能再上去了。杨海能爬,在我六七米高的上面,当然,我们是交错着的,他东我西,或他南我北,这样避免树枝掉下来砸到我。
我和杨海相处有五六年了,把我和他拉近的是一件事。一天下午我去田里看秧苗,走上一个小斜坡,看到一条沟渠里一双脚成V形一张一合,像把要剪破天空的剪刀,然后又像作揖,上下摆动。我走近看,是杨海,他肚皮朝上,双肩夹在沟渠里,手无法动弹,舞动脚也不能让他起身,像一只石板上肚皮朝天的乌龟。我忍着笑,像摇一截树桩,花了五六分钟才把他拽出来。他说挣扎十多分钟了,因为怕招来很多人而丢脸,一直没有喊,只用脚来求救,还好碰到我。
“昨天体检,你的也是脑血液不稳定?”杨海说完,手上锯断了一根树丫,树丫掉到地上,槐树下的杜春把它拖到一边。
昨天县疾控中心来村里体检,检查心脑血管,女的外加妇科。检查心脑血管的时候,脑袋上套一个头盔一样的东西,上面两根线,连到一个收音机大的显示器上。显示器有两个表盘,上面有一些刻度,刻度每隔一段标着数字,一根红指针在上面摆来摆去,像根拒绝的手指,看不出什么意思,只有医生才看得懂。我问看显示器白白胖胖的男医生,我的脑血管有没有问题,他说没什么大问题,只是脑供血有些不稳定,脑子里的影像不清晰。我站在一旁,见他对好几个人都这样说。那指针,还真是根否定的手指。我们问要不要医治,他说不用。
“是啊。”我说,顿了两秒,又说,“难道全村人都一样?”
杨海扒开脸上的一条树枝说:“有两个不一样,喏,一个是正在看我们的郑小泉。”他拱着嘴向远处的郑小泉指一下,“另一个是傅永会。”
傅永会住在村北边,七十多岁,听说是北京来的知青,回不了城,在我们这里娶妻生子,跟女婿女儿生活在村里,大儿子在市医院工作。土地承包到户时候他当过两年村主任,好土地分给自己,粮食年年丰收。从村主任位上下来,村里好多人都恨他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他画起画来,有一年还拿到市里展览,成了画家。我没见过他的画,见过的说,他画的都是些破房子、枯树、光屁股女人。
人们都说,他为什么不画村里的洋楼、白花朵朵的大槐树和穿衣服的姑娘,这分明是要砸我们“文明村”的牌子,有人说他老不正经。这几年,他对村里人也不大来往,几乎没有朋友,路上见了,一副冷冷的态度。我们都认为他傲气十足,对他慢慢由不喜欢,变成讨厌。男人们见他,向地上吐口水,女人见他,远远地让开,巷子里实在让不开,贴墙站着,等他过去了才走。
“这两个人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?”杜春仰头问杨海。
“这两个人脑子影像清晰,连小问题都没有,正常得不得了。”杨海笑嘻嘻地说,一片树叶挡住他的鼻子,让他的表情残缺不全。
“你听哪个说的?”杜春又问。
“医生刚要上车,我问了,看仪表盘的医生说的,就是白白胖胖那个。”
“一个精神病,一个老不正经,真是怪了。”我说。
“难道我们也要变成精神病和不正经,血管和影像才正常?”杜春自语似的说,手里提着一根树丫砍削着,他的话我们还是听见了。
杜春是我奶奶堂妹的孙子,和我是表兄弟,我们常聚在一起喝酒闲聊。杜春七年前大学毕业,在城里做了两年的快递员,辛苦且工资不高,回来了,在自家山林围下一片地做养鸡场,父母帮照看,他说现在有两百多只鸡。有时我家里要用鸡,去他那儿,他都是便宜价给我。他喜欢吃动物肠子,猪肠、羊肠、鸡肠、鱼肠,就连菜叶的茎须也不放过。他吃过所有能吃的肠后,觉得还是鸡肠更入口,他说:“鸡肠的那股香和嚼劲,有种说不出的好。”我有时想,他是否因为喜欢吃鸡肠才养鸡。
阳光穿过树梢,来到身上,像一件轻薄衬衫,不轻不重。每经过这里,我都会停下脚步,仰头看树一眼,随后,目光下移,停留在它根旁的土地上。
风呼呼吹,几片橙黄的树叶斜斜地飞,像受伤的蝴蝶,有的落到西边菜地,有的落到东边晒场。风并不甘心,仍不倦地翻动着树叶,像要把它们叫醒,让它们重回枝头。
槐树根离晒场边一米多,在矮处,晒场比它高七八十公分。槐树比我岁数还大,大很多,也就是说,它所看到的人事比我看到的还多。树根一抱还围不过来,两米以上枝丫分开,向四周伸展,高达二十多米,每到春夏季,枝叶繁茂,阳光落下来,大半个晒场被它遮挡。蜜蜂在白色的花蕊上停留、飞舞,热热闹闹,仿佛是它们的露天会场。我前面八九十米远,就是我家院门,站在院门口能闻到飘散而来的槐花香,有许多蜜蜂飞过头顶,奔向槐树。
杨海曾对我说:“是该修理修理了,我那块菜一到秋冬季落得到处是树叶。”
树叶落到地里倒是小事,主要是这几年烧柴贵了,砍下一些枝丫,也算减少点开支。厨房里虽然用上了电,但也有不方便的时候,比如请客吃饭,可以多烧两个炉子。
这棵树第一次修枝,是在五年前,那一次是杨海上树,我没有上去。这一次,我应该上来,人一辈子总不能三米高都突破不了吧。不过,头是真的晕,我的左手紧紧抱着树干。
该砍的几乎都掉落地上,整棵槐树稀疏了些,地上堆满了枝干和树叶。我和杨海从树上下来。
槐树下是家里的菜地,听父亲说,爷爷死在地里后,奶奶没有再种菜,在上面栽了三棵槐树,一棵两个月后枯死了,一棵长得慢,两三年不见长一截,最后也干枯而死,只有这棵,倔强昂扬,长势良好。父亲说,这棵树脚正是我爷爷侧躺的地方,“他嘴和鼻子都流血,可能是你爷爷的血滋养了这棵槐树,才让它长这么高。”如果真是这样,每朵花、每片树叶都有他血的养分。看着地上砍下的枝丫,身上的肌肉一下收紧。转念想,不可能吧,它早被五十多年的岁月冲走了。
爷爷生前,上过初中,在村里是唯一的高学历,时常跟人讲古论今,言语直率,说这人不是,那人不是,得罪了村里好多人,人们看不惯他夸夸其谈的样子,同时对他的不留情面报以怨恨。五十二年前,村长听信一个神汉的话,让每家每户从分到的粮食里匀出一碗,或大豆,或玉米,聚拢来烧成灰,撒到田地里,边撒边念几句词,这样可以增加粮食收成。如果谁没贡献一碗粮食,生产队便以破坏生产之罪,给予惩罚,来年粮食少分三斤。爷爷不仅不贡献一碗玉米,还在村里的墙上贴了大字报,上面写着:粮食增收,靠的是粪肥、勤快,不是靠巫婆神汉,献出一碗米,全家少吃一天粮。王良才。村长认为,爷爷不仅想让群众饿肚子,而且还煽动人们反对增产增收,不能轻饶,便撤下墙上的大字报,来到家中找爷爷,奶奶在做晚饭。奶奶以为他只想批评爷爷几句,便没放在心上,告诉他爷爷在菜地里浇水。村长从家里出去,进了几户人家,叫上几个人,一起去菜地,边走边说爷爷居心不良,敢写反动大字报,简直翻天了。村里好多人早就对爷爷卖弄学问的样子见不惯,听了他的话,恨得牙痒痒。
爷爷提着水桶准备回家,村长把大字报展开在他面前,问是不是他写的,他说是。村长给他脸上一巴掌,其他人蜂拥而上。他被打倒在地,五六个人拳打脚踢长达二十分钟。他口鼻流血,最后被一个男人踢下晒场,滚到地里,蜷缩着。村长见他不动,怕闹出人命,才叫身边的人回去。奶奶赶到,把他背回家,午夜时死在床上。两天后,奶奶疯了,半年后跳了崖。
杨海跟杜春一起削带叶子的枝丫。我回家骑来那辆破摩托,把削下的枝丫捆到后座上,一趟趟运回院子里。
我第三趟回到晒场上,有三男两女五个小孩在晒场边摘树叶玩,其中一个是我女儿小双,八岁,上小学二年级,另一个男孩是杨海儿子,跟我女儿同岁,其他三个我不认识。村里一百多户人家,这些年,我很少走门串户,小孩一茬茬出生,八九岁以下的小孩,我多分不清谁是谁家的。杨海站在树根旁,一只脚搭在晒场边,嬉笑着问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:“你祖祖还画不画不穿衣裳的人呢?”小男孩手里捏着一片树叶,低着头,把脸侧向一边,不回答他。他还在追问:“说啊,他还画不画?”杜春提着一根枝干砍削,脸上微笑着。
孩子低头站了一会儿走开了。另一个比他大一两岁的男孩手里捏一根枝条,走近杨海,眨着一双大眼睛说:“他刚才跟我们说,他祖祖说了,昨天医生检查,好多人的脑子里有许多小人,就他祖祖跟那个疯子没有。”
“他真这样说?”杨海脸上的笑消失了,扭头看向晒场边低头折树叶的小男孩,杜春手里停下来,看着杨海面前的男孩。
“不信你问他。”男孩手指一下远处的小男孩。离男孩两米远的杨海儿子对杨海说:“他真说过。”

2
“老头说我们脑子里生娃娃,这不是侮辱人吗?”杨海刚坐到饭桌边就说,他好像相信了孩子的话。天色已黄昏,院子里风噗噗地吹动墙边的槐树枝,刘梅把一碗猪排烧土豆端上桌,浅笑着看杨海一眼,走出去了。小双和杨海儿子把菜扒到饭碗里,坐在门外吃,边吃边叽叽咕咕说话。
“他说我们都是女人呢,脑子里有小孩做窝。”杜春双手拄在大腿上,咧嘴笑。我对傅永会没什么接触,即使路上碰见,也不打招呼。他好像对谁都看不惯,我们也看不惯他对人冷冰冰的样子,能画几幅画有什么了不起啊。说实在的,我对画画也不懂,在村里画光屁股女人,终究是伤风败俗。他把我们都说成女人,真是过分。
“饭吃完,我们去问问他,到底我们脑子里有没有小人。”杨海喝下一口酒说。
我说:“你俩去就行了。”
“怕什么,拿出你以前的狠劲儿,在他脸上吐一泡口水。”杨海又接着说,“我还记得,前年,你提着砍刀把阿三撵得满村跑,想不到你平时温温和和的,那次倒是把我吓着了。”他呵呵笑着。
我用筷子指指饭桌说:“往事不提了,吃菜。”傅永会没对我怎么样,我怎么会朝他脸上吐口水,杨海把我想成什么人了。
我说:“别乱来,好好跟他说。”
“当然,我咋会乱来,不过,人要对得起我们村,他一个外地人,来到我们村,不能砸了我们‘文明村’的牌子,这是良心,他咋就不懂呢?”杨海把一块瘦肉塞进嘴里,筷子摆到碗上,腮帮勤奋地磨动着。他的热心肠在村里相当耀眼,十多年前的一天傍晚,他在一个山崖下翻地,一辆拖拉机飞下对面三四十米高的山崖,眼睁睁看着拖拉机落在斜坡上,车斗里的五个人被扔出来,在斜坡上木头一样滚。他赶忙丢下锄头跑上斜坡,一个个察看,最后背起一个满脸血污的女人往镇上走,路上不管碰到谁都说赶快去救人。后来有人笑话他,只会救女人,他咧嘴笑,“莫乱说,她都不会哼叫了,救人先救重。”幸运的是,那五个受伤的男女,医院里住了三四个月,最后都陆续出院。
刘梅坐到我身边,端着一碗饭,默默吃菜。刘梅不是话多的人,我们男人说话,她一般不会开口。
我给杨海和杜春添了一回酒,杜春没有接,我自己的酒杯添了一点。我喝酒少,不想醉酒后身体难受。我原来就交代过的,能喝多少是多少,谁劝酒,谁他妈滚蛋,这俩家伙还算有点耳性,我交代后,没劝过酒。
杜春端起酒杯向杨海敬酒,说他是他婶婶的救命恩人,很感谢。杜春婶婶就是出车祸时杨海背到镇医院的女人。杜春说:“有你这样的好心人,是村里的福气。”杨海笑得脸上褶子乱爬,摆摆手说:“一村人,应该的,应该的。”说完跟他碰了杯。
杜春端着酒杯转向我:“杨海夹在水沟里,你救了他,是我恩人的恩人,也是好人。”我笑着说:“救人一命胜过喝酒吃肉。”跟他碰了杯。杨海尴尬地笑笑也向我敬酒。
杨海像要摆脱水沟事件,把话题转到傅永会上。“傅永会以前为什么留在村里不回城?”他脸上似乎有答案,只是问我们是否知道。他脸没有红,但醉意横行。
我摇摇头。“为什么?”杜春反问他。
“没结婚,他媳妇肚子就现形了,哪回得了城。”他喝一口酒说。刘梅白了他一眼,对刘梅的白眼他没放在心上,呵呵笑着。这个我倒没听说过,也许是真的,城里人谁会平白无故留下来。
“这就叫‘一失足成千古恨’。”杜春说。
恨不恨,只有他心里知道,我没法判断。杜春沉默几秒说:“有一次在娱乐场上,他跟我大叔聊天,我站在旁边,他一个人叨叨个不停,说他儿子小时候如何如何懂事,在医院里研究的项目如何如何高端,还有,他一张画别人给了几千的价,我大叔只顾点头,他整个话傲气十足,显得自己多了不起,好像别人渣渣都不是,我听了想吐,转身走开了。”
这个我没法说,因为我几乎没见过他跟谁在一起聊天。

以上皆为节选,
详情请参阅《四川文学》2022年1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