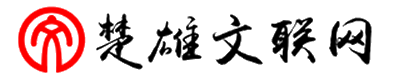作者:李光彪
昨天晚上,雷声轰隆,炸破天空,雨哭哭啼啼,下了一夜。
我不知什么原因,做了一夜的恶梦。
清晨去上班,看到办公楼前湿漉漉的广场上,那棵差不多有办公楼高的雪松被雷劈头盖脸拦腰折断,枝叶有的落到了地上,有的依然打断骨头连着筋,如挂在“光杆司令”身上须须柳柳的破衣服,一副伤心伤肝的样子。
陆陆续续上班的不少同事走过路过,都觉得很奇怪,我是一棵被移栽进城市的树,也为那棵半条命的雪松而忧伤。此刻,故乡的树就从我记忆的深处源源不断冒出来,浓荫如盖长满了我记忆的天空。那一棵棵高的、矮的、粗的、细的,叫得出名字的,叫不出名字的,一山山、一箐箐、一坡坡绿油油的树,是山里人祖祖辈辈的衣食父母。一年四季,春夏秋冬,日日夜夜,山里人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树,少不了树。
老家的人就连起名字,也少不了带个“树”字。乳名有叫小树宝、小树生、小树梅、小树兰之类的,学名有叫李树荣、李树成、李树花、李树美之类的,都与树有关。尤其是婴儿夜间啼哭不乖,就会拜树为“干爹”,向树“讨名字。”此时,父母就会请先生用红纸写一张字条,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贴在村口的大树上。我们一群早起读书的娃娃看见,就会好奇地盯着红纸条念:“天青青,地绿绿,我家小儿半夜哭,君子过路念一念,一觉睡到太阳出。”故乡的每一个孩子对这首童谣耳熟能详,都是念着树上的“小儿郎”红纸条长大的。
老家的人并没有高深的文化,也不懂修辞手法,却经常以树拟人,以人喻树。说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是“木头木脑”,说那些脾气倔犟的人是“纽松桐”,说那些一根葱的小伙子是“白杨条”,说那些窈窕淑女是“风摆柳”,说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是“老枯树”,说那些偷奸耍滑站在旁边不干活的人是“树神”,说那些成长缓慢的人是“树骨桩”。不论是褒义贬义,大家都不计较,直来直去,说说笑笑,以树取乐,幽默诙谐。
老家的村庄,只要有方寸土地,都会栽上树。每个孩子呱呱坠地,父母都会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栽下一棵树,预示着树长多大,孩子就会长多大。特别是端午节那天,家家户户都遵从“五月端午,栽棒槌都会成活”的古训,倾巢出动栽树。你家栽,我家栽,家家户户都载上桃树、梨树、板栗树、核桃树、山楂树、柿子树、香椿树等果木树。不仅端午节栽树,春节还要在院子里栽一棵又高又直的云南松,欢欢喜喜过年。可是,那时没有生根粉,移栽技术落后,“年松树”只是节日的一道风景,点缀完正月十五元宵节,渐渐枯萎的松树就被当作烧柴晒在柴码垛上了。
“前人栽树,后人享福。”爷爷生前在菜园埂上栽的那棵被村里人称为“树王”的柿子树,却令我们眼馋。柿子树又高又大,宛若一把大伞,到了火把节前后,柿子逐渐成熟,我们兄弟姊妹几个,就会互相推着屁股,偷偷爬上树,摘几个绿色的柿子,放在火上烧吃。或是做个记号,悄悄埋在水稻田里,五六天后再掏出来,洗干净,柿子的涩味没了,吃着又甜又脆。转眼到了中秋节,柿子全部成熟,阿爹却看得很紧,砍很多刺,把柿子树脚栅栏得严严实实。可是,我们另有高招,就地找一棵瓜架当梯子,爬上树和鸟争食那些早熟的柿子。收获的时候,阿爹哼着调子,把柿子一筐一筐摘下,绿的削皮晒柿饼,黄的柿子与酸木瓜一起放进土陶罐里。五六天后,柿子捂熟,阿爹又一层稻草一层柿子小心翼翼装进箩筐,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挑去马街卖。因为元谋马街县城天气炎热,喜欢吃柿子的人多,总是比在家门前的狗街、猫街能卖点好价钱。阿爹每年去马街卖柿子回来,都会顺便给我们兄弟姊妹带回几粒糖果和几个酸角,让我们解解馋。
但对于我来说,除了柿子树,最钟爱的还有院子里那棵和我朝夕相处的杏子树。
村里人常说,我能走出大山,全靠有阿妈这棵弯腰树。可阿妈却说,我能走出山外,全靠院子里那棵弯弯的杏子树。
杏子树是阿妈从山背后嫁来那年,从外婆家带来的“嫁妆树”,也是阿妈亲手栽的结婚“纪念树。”
那时,杏子树和阿妈一样年轻,结出的杏子跟桃子一样在。阿妈把杏子背到狗街和猫街小镇上,总是能卖好价钱。每次回来,少不了要给我买回几粒糖果,或是买回全家人生活用的煤油盐巴和肥皂洗衣粉。记得我第一天上学背的书包、写的铅笔和字本,就是阿妈用卖杏子积攒下来的钱替我买的。可是,年幼无知的我见阿妈不在家里时,就约来村里的小伙伴,把背柴用的背索、皮条拴在树丫里荡秋千,或是攀上树丫又摇又闪,把树当轿子坐,压得杏子树弯弯的,树叶触到了地上,阿妈回来看见,就用吆鸡棍抽我的屁股。当我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时,阿妈总是把我拉进她的怀里,心疼地对我说:“莫哭了,听阿妈的话,要是杏子树死了,以后阿妈就没有钱给你买书纸笔墨了。”
直到后来,随着年岁增长,我用阿妈种菜、养猪、卖杏子积攒下来的钱读书,才明白阿妈为什么要用吆鸡棍抽我的原因。可惜,院子里那棵弯弯的杏子树再也无法长直,像阿妈驼了的腰。
在我的眼里,厚厚的大山就像一道铜墙铁壁,把小小的我禁锢在山里;高高的大山就像一道石门槛,把小小的我拦在山里;延绵不断连着天边的大山就像一把锁,把我紧紧锁在山里,也把树锁在山里,树和我一样是山中的一员。树不惧风寒,不怕酷暑,悄悄地、静静地、默默地长在山坡上、箐沟旁、小河边。只要有方寸能站住脚跟的土壤,树就会生根、发芽,撑出一片绿荫;只要能接纳一滴雨露,一缕阳光,树都会开花、结果,树,就像山里人一样,世世代代繁衍生息。树的一身,从头到脚,都有用处。嫩叶可当菜食,或当茶叶泡水喝;躯干直的可做木材,弯的可当烧柴;根可做药,能治百病。山里人不仅生产用的锄把、刀把、犁把少不了树,而且,生活中的起房盖屋,做床打柜,凳子、桌子、甄子、水桶、砧板瓢勺都是用树制成的。
树是山里人最亲密的朋友,每个人到了男婚女嫁的年龄,结婚时,男的少不了要用最好的树做一张红油漆喜床,女的少不了要用上等的树做一张红彤彤的嫁妆柜。真是人人如此,活着离不开树,死了也少不了要用树做成棺材陪葬。生生死死,人与树相依相偎。
树和我家祖祖辈辈有缘。爷爷是旧社会时村里的头人,村庄背后的那座山叫凤凰山,既是村庄的坟山,也是村庄的靠山。村庄里都有约定成俗的规矩,一年到头,实行家家户户轮流看管“拿山”。可是,有的人家看到偷砍树的人,却撕不开面子,认为都是“同喝一井水、同烧一山柴”的村邻乡党,抬头不见低头见,本着“教育为主,处罚为辅”。因此,年年封山,年年很多树被人偷砍。爷爷为了护住村后那山树,就假戏真演,让奶奶在全村人吃午饭时故意去偷砍村后的树,被“拿山”的人抓到后,并按村规民约杀了自家的猪,请来全村人来家里白吃了一天,以示惩罚,明示众人,树是山里人的命根,不可轻易乱动。从此,爷爷以身作则护山护树的故事,在十乡八里流传至今。
叔叔是个木匠,一把斧头,几把锯子,几个推刨,几支凿子,帮人家架梁竖柱,安门做窗,制作家具,干了一辈子的木活,吃了一辈子的“树饭”,是个响当当的手艺人。
我也不例外,儿时生活在山里,享了不少树的“福”。春天,嫩生生的香椿芽可以弥补我的书纸笔墨钱;夏天,那条最渴望的游泳短裤和避暑背心,就是用树上采下的“雀嘴茶”“乌鸦花”换来的;秋天,那瓜菜当饭的岁月,就是从山上砍来椽子木头换来的粮食度过的;冬天,上学提的火盆里暖烘烘的炭,就是用树疙瘩烧成的。和树在一起,就像和父母在一起,和哥哥姐姐在一起,温暖又幸福。
在山区老家,水是生命之源,火也同样是生存之源,取暖、烤蒸、煎煮都少不了火。生火少不了柴,每年到了寒冬腊月,生产队就会统一放几天假,停工让各家各户背烧柴。大家按照村里的规定,互相邀约,蚂蚁驮盐似的涌向指定的山头,间伐那些成不了材、弯弯扭扭的灌木林,背回家晒干后当柴烧。由于规定砍柴的时间较短,在背烧柴的那几天里,是全村男女老少最辛苦、最忙碌的时候,家家都磨刀嚯嚯,拎着柴刀、斧头,穿上羊皮褂,带上皮条、背索、背板、背架,你追我赶,一趟又一趟来回上山“狗撵羊”似的砍柴背柴。几天下来,家家户户的门外就垛起了大堆大堆的柴码。柴码垛也就成了衡量劳动力强弱和农家勤劳的尺码。但是,砍柴也有规矩,坟山、靠山属于封山,是不可轻易乱砍的。在哪一座山砍柴,必须由村里共同商议决定,然后在规定时限内到指定的山头砍柴。而且,有人专门用一根“六尺杆”挨家挨户丈量柴码,不能多砍。如果谁家遇上红白喜事,就适当放宽一点尺码,多给一点指标砍柴。多少年来,人保护着树,树养育着人,情同手足,相伴相生。
树和我的成长一样,也经历过风风雨雨,也有过惊涛骇浪。“大炼钢铁”的年代,大片树木被无辜砍掉。进入八十年代以后,村里除坟山继续统一管理外,大部分山都像土地一样承包给了各家各户。随着烤烟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,不少人生怕政策改变,以砍柴烤烟为名,杀鸡取卵,蚕食了不少的树木。政府立即出台政策,开始对烤烟煤进行补贴,推广改灶、改厕、改电等工程,那些“鸡窝灶”、“老虎灶”被洗心革面,电通进了农家,沼气得以利用,柴火便成了替补的燃料。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一场洪灾,警醒了人类,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上了议事日程,开始实施“天保工程”、“退耕还林”补助农民钱粮等政策。前几年,又实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,使山有其主,树有其母,很多人明白了树是人类的朋友,是人类生存的衣食父母,明白了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无柴烧”的道理。自觉地护树、爱树、种树、管树,把原来一直当柴烧的树木,也当作田地里种植的庄稼,精心管护,潜心经营。有的买山、租山、包山,有的种桉树、种果树;念起了“山经”,唱起了“山歌”,把致富的钥匙伸向了山门,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树林。
这些年春节回老家,我突然发现村里的那些柴码垛矮了很多,少了很多,渐渐消失了,袅袅炊烟也几乎看不到了。
如今,老家的人也进城打工的打工,读书的读书,树也跟着人源源不断进城。我所在的城市在不断创建园林城市,生态城市、森林城市、旅游城市、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,街道旁、广场上、公园里、小区里、龙川江边、青龙河畔,每年都要栽很多大树。这些树都和我一样,是上了年纪的树,大多数都水土不服,冬天害怕霜雪,还要穿衣戴帽。倒是我认识的那些为数不多豆瓣香、黄连木、滇朴、雪松等三四种本土大树,该落叶时落叶,该发芽时发芽,告诉我春夏秋冬季节。
关于这些大树的来龙去脉,听说是来自于乡村修水库、修公路,树必须牺牲让步,所以大树被移植进城,也有的人说大树是被人偷盗买进城的。不管大树怎样进城有多少版本,我没有深究过,但这种吹糠见米的场景我也目睹过不少。
我也是一棵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树,偶尔写点小文章,很多人夸我有文才。我笑笑:不错,我是木材的材,比文才的才还多过木字呢。有时,自己不知道城市生存的法则水有多深,说话像木材一样直来直去,也得罪了不少人。不少朋友善意提醒我,说话要像那些缠在树上的藤蔓学会绕。但树一样禀性的我客居城市多年,每当看到那些水土不服的大树,栽了死,死了又栽时,如痛失亲人,就会想起老家的那一座座山,那一棵棵亲密无间的树。
不知不觉,就到了中午下班时间,我走出办公楼,想不到“雷打树”已被清除,重新栽上了一棵几乎一模一样的雪松,很多人都和我一样,为这种神速的“移树补景”大吃一惊。而且,那棵补位站岗的雪松枝繁叶茂,彻底颠覆了我长期以来“树挪死”的陈旧观念。可令我纳闷的是,那些和我一样土生土长的树,都来自远山和村庄,它们都是古树、老树,被活生生挖断根,“妻离子别”强行移栽进城,树干上挂满了“打吊针”的输液袋,就像我患了癌症透析时满身插满针管的岳母,心中的疼痛只有岳母知道。
没过几天,办公楼里爆炸出一条与“雷打树”有关的消息,主事的领导被纪检清走了。
人树相依偎,树的伤痛,只有树知道。
2021年8月19日
[作者简介] 李光彪,笔名虎三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。散文作品见于《文艺报》《云南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散文选刊》《读者》《青年作家》《中外文摘》《天津文学》《长江丛刊》《边疆文学》等。已出版《随笔漏拾》《沾满泥土的情绪》《母亲的气味》3本书。《故乡的眼睛》等9篇散文入选全国高中、中小学语文测试题。《一根稻草》等8篇散文入选王剑冰、贾兴安、耿立等主编的年度《散文优秀作品年选》。通讯地址:云南省楚雄市阳光大道文化活动中心楚雄州文联
联系电话:13908782733